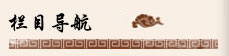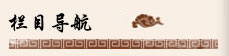随着对玉小石的“华丽”转型之路的探寻逐步白热化,小编在此一直有一个疑问。
为什么儿时的护身符中,玉石会占据一席之地呢?
换言之,以“玉”当作能够趋吉避凶、保佑家人平安的吉祥物的风俗,从何而来?
答案就在柳生的故事里。欲知后事如何,请诸君随我来。
时间:春秋战国
人物:柳生、柳父、柳母、君主、女子(柳妻)
关键词:弄璋;组佩;贬官;赠玉
某年某月某日,随着阵阵啼哭声,柳家迎来了家中的第一个嫡子。柳父带着初为人父的复杂心情看着这个孩子,就在这时,柳母微弱的声音传来:“快,拿玉璋…”柳父急忙跑到柜子前,拿出了一块玉璋让孩子把弄。柳母才安然睡下。
——让初生儿弄璋的场景,实际上暗含了为人父母寄寓孩子长大为官为君的愿望。
克己复礼:“既服,习容观玉声”。 ——《礼记·玉藻》
柳生长大后,果然不负众望,成功做了官。朝服要求佩戴组佩,组佩如下图所示。佩玉要求他行走时,左边发出宫羽——也就是现在1、6的乐音,右边发出徵角——也就是现在5、3的乐音。柳生深感作为一个“君子”的责任和担当。之所以佩戴组佩,是因为君子要“节行止”,践行“克己复礼”的君子之道。诸位看官或许会想问,组佩和“克己复礼”有什么关系呢?其实,“左宫羽、右徵角”的要求可不低,就组佩而言,它要求组佩的质地、形状、组合要规范而讲究。

(组玉佩—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)
下图所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组佩。由中间从上往下看,第一排为玉珩,玉珩以下为玉瑀,第三排是玉花,第四排与第二排所用的玉相同,最后为玉珩。第二排左右两边呈长方形的玉叫做琚,最后一排末端尖形似牙齿的玉叫做冲牙,左右两边形似雨滴的为玉滴。组佩的标配向来少不了图中的珩、琚、瑀、冲牙,这是材料上的规范而讲究。
“趋以采齐,行以肆夏,周还中规,折还中矩,进则揖之,退则扬之,然后玉锵鸣也”
——《礼记·玉藻》
除此之外,对佩玉者的行为也有所要求。《礼记·玉藻》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是,若想让玉发出锵鸣的声音——小步快走要符合《采齐》的乐章,平常行走要符合《肆夏》的乐曲,周旋转身要中规,弯腰俯身要中矩,往前走身体要稍前倾,往后退身体要略后仰。处在如今这个以“方便、快捷”为原则的时代的我们或许很难理解,走个路为什么会这么麻烦呢?实际上,古代的“君子”不仅要内心光明磊落,举止也要温文尔雅,这样才能符合一个有德行的君子形象。
君臣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。柳生也因无意间触犯龙颜而被贬官。贬官的三年之期到了,柳生不敢离去,他在等待君主的使者捎来信物,如果君主赐给他“环”,他就能收拾行囊,回家了;如果赐的“玦”,那柳生只能以死谢罪了。正如它们的读音一般,下图的完整的圆环就叫做“环”,意味着“还乡”;左图有缺口的“环”叫做“玦”,意味着“断绝”。此为君子重耻的体现。那么各位希望柳生被赐玦还是赐环呢?
重信:“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” ——《诗经·卫风·木瓜》
根据“主角光环”定律,柳生这个时候可不能死,故事戛然而止好生不快。果然,君主赐环,柳生归来。见到自己心爱的姑娘,得知异地三年,女子还在等他,柳生十分感动,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玉佩送给女子,许下承诺,改日迎她进门。在我们的故事里,柳生的人物设定是可君子,君子自然信守承诺,把女子娶进门。柳母赠玉,表达对他们的祝福。——以玉作为信物,表明君子重信。
小编:故事到这里就“全剧终”了,让我们预祝柳生一生平安幸福。在柳生的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里,玉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。可见玉对于古代的君子来说,必不可少。“君子之心,比德于玉”,正是如此。此外,人们也会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玉的身上,以玉作为定情信物或者儿时的护身符,玉就仿佛具备了灵性。因为相信,自然成说。
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一楼展厅,常年展出玉璋、玉环、玉珏、玉握等精美玉器,天地灵气等你来看呦~
参考文献:
[1] 朱怡芳. 文化密码:中国玉文化传统研究[J].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(美术与设计), 2010(2):114-118.
[2] 张丽. 《说文解字》玉部字显示的古代玉文化意识[J].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 2008, 27(4):113-117.
[3] 李婵, 徐传武. 《诗经》中的玉文化[J]. 东岳论丛, 2011, 32(3):126-128.
[4] 刘素琴. 儒释道与玉文化[J].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, 1994(1):38-45.